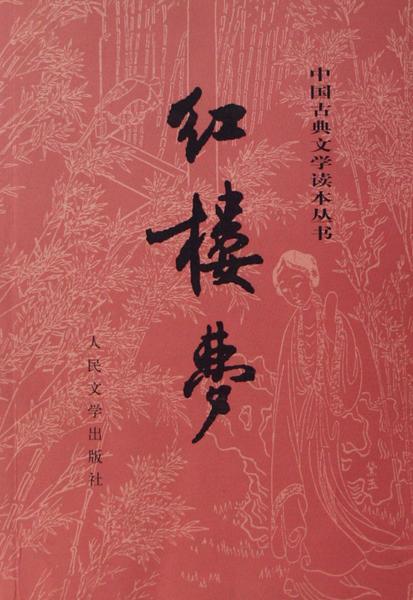
贾环是《红楼梦》中一个尴尬人物。说他是主子,却是一个“贱妾”所生,说他是奴才,却是贾政的亲生儿子,同贾宝玉是同父异母的弟弟,他的同胞姐姐探春也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姐。在一般读者心目中,贾环长相似乎与贾宝玉判若云泥,又有不少劣迹,委实不可爱,岂但不可爱,甚而至于可鄙。但仔细地想一想,读者心目中贾环的形象,不一定是曹翁原本所要创造的形象,有些读者没有深入理解曹翁笔下的奥妙,所以对贾环形象的理解出了偏差。
《红楼梦》第二回里,冷子兴向贾雨村介绍贾宝玉,借贾宝玉周岁“抓周”时抓着脂粉钗环、七八岁时总结出来的“女儿男儿的骨肉论”,把其贬低了一番,而介绍贾环,则这样说:“政公既有玉儿之后,其妾又生了一个,倒不知其好歹。”这里,曹公是有意不给贾环下断语,好让读者以后去思考。第十八回里,贾府中谒见元春的,有点头脸的人都写到了,贾宝玉更是重点描写对象,但写贾环,只是这样一句:“贾环年内染疾未痊,自有闲处调养,故亦无传。”这一交代,也可以这样理解:贾环若在场,贾元春也势必试一试他的文才,而他不在场,当然无所谓试不试了。贾环究竟有没有什么文才,给读者留下了悬念。
第二十五回里,王夫人趁他下了学让他抄《金刚咒》。《金刚咒》在王夫人心目中是十分神圣庄严的,估计贾环抄写是胜任的,才让他抄写。这说明,贾环也是一个有文墨的人。第七十七回里,贾政也曾对贾环、贾兰说过,“宝玉读书不如你两个”,这说明贾环读书也用了劲的。第七十八回里,贾环作的《姽婳词》受到众幕宾赞赏。众幕宾也许有阿谀贾政之嫌,但贾政也说“还不甚大错”,当然他也要谦虚一点,讲讲贾环之诗的缺点,而缺点只是“终不恳切”。可见贾环的文才还真是不错的。
贾环其实也是一个聪明人。第二十二回里,贾元春差人送出一个灯谜儿,要众姐妹兄弟侄子们猜。结果是其他人包括贾兰都猜中了,只有迎春和贾环没有猜中,没有得到元春所赐的礼物。迎春无所谓,贾环觉得没趣。这里不应该理解为贾环和迎春一样愚钝。有些谜语的谜底,本来不止一个标准答案,他猜出的也许是另一个,亦是可以的,只是元春不认可,所以没趣;还可以理解为他是故意猜错,他不与元春他们合作,与他们合作是没趣的。
贾环岂只是不愿意与贾府的人合作?他还要表达自己的不满甚或反抗。同在第二十二回里,贾环奉元妃之旨所作的灯谜儿是“大哥有角只八个,二哥有角只两根。大哥只在床上坐,二哥爱在房上蹲。”这样的怪灯谜儿,连元妃都没有猜出,还要太监代问答案。这个谜底是枕头和兽头的灯谜儿很有意思。它实际上是影射宝玉和他贾环自己。一个有角八只,强势得很,而又受人宠爱,但终究只能在床上坐坐。一个只有两只角,比较而言显得弱势,也不招人喜欢,只好蹲在屋脊;既孤独地蹲在屋脊,倒要看看受尽娇宠的人做些什么,有什么样的结果。贾环的不满甚或反抗情绪,在这个灯谜儿表达的十分明显。
贾环当然应该不满,应该有反抗情绪,因为他没有得到他应得的权利;他是奶奶不疼、父亲不爱、婶娘势利眼、王夫人姑侄更是处处贬抑压制的人。宝玉被允许在大观园里和姑娘们一起居住玩耍,贾环却被摒在门外。第二十三回里有这样的描写:“贾政一举目,见宝玉站在跟前,神采飘逸,秀色夺人;看看贾环,人物委琐,举止荒疏……”这是贾政的感觉,是不“客观”的,俗话说“恨人丑”,自己不喜欢的人,自然也丑了,不管其实际情况是怎样的。贾政的眼神和情绪,贾环当然看到和领悟到的,对这样一个父亲,这样一个家庭,贾环何能爱得起来?第二十四回里,贾宝玉去贾赦处请安,被邢夫人拉去到炕上坐,百般怜爱。而贾环、贾兰来了,邢夫人只让坐在椅子上。“贾环见宝玉同邢夫人坐在一个坐褥上,邢夫人又百般摩挲抚弄他,早已心中不自在。”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,想没有仇恨也不可能。
如果说贾府除了自己的母亲喜欢他,亲姐姐探春关心他(暗地里,大庭广众之中还不便),余下的就只有丫环彩霞了,但宝玉还要横刀夺爱。第二十五回里,贾环奉王夫人之命在抄写《金刚咒》,丫环彩霞在服侍他。宝玉从舅父王子腾家喝酒回来后,受到王夫人千般娇宠,在其身后躺下,又叫彩霞去服侍,还“一面拉他的手只往衣内放”。在这种情况下,贾环想不忌恨宝玉也不行,在逮着机会的情况下,故意拨翻烛台,烫伤宝玉,是情理之中的。第三十三回里,金钏被王夫人逼迫得跳了井,他诬陷宝玉,使得宝玉遭受贾政毒打,手段是毒了点,却也在情理之中。
第八十五回里,贾环弄洒了凤姐给巧姐熬的药,凤姐大怒。赵姨娘也大骂贾环。贾环愤愤地说:“我不过弄倒了药铞子,洒了一点子药,那丫头又没就死了,值得她也骂我,你也骂我,赖我心坏,把我往死里糟蹋……”贾环满腹委屈,也应该满腹怨恨,这样的人何可能没有反抗情绪?
综上所述,贾环其实是一个不乏才学、能独立思考、世事洞明而又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形象。一般读者鄙视他,是因为受了《红楼梦》中其他人物对他的态度的影响。试想想,说他可恨,他比伪善人王夫人可恨吗?比心狠手辣的王熙凤可恨吗?说他可鄙,他比老牛要吃嫩草的贾赦可鄙吗?比要粗俗有多粗俗的薛蟠可鄙吗?要表明对他的态度,最多也只是“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”吧。(黄三畅)
